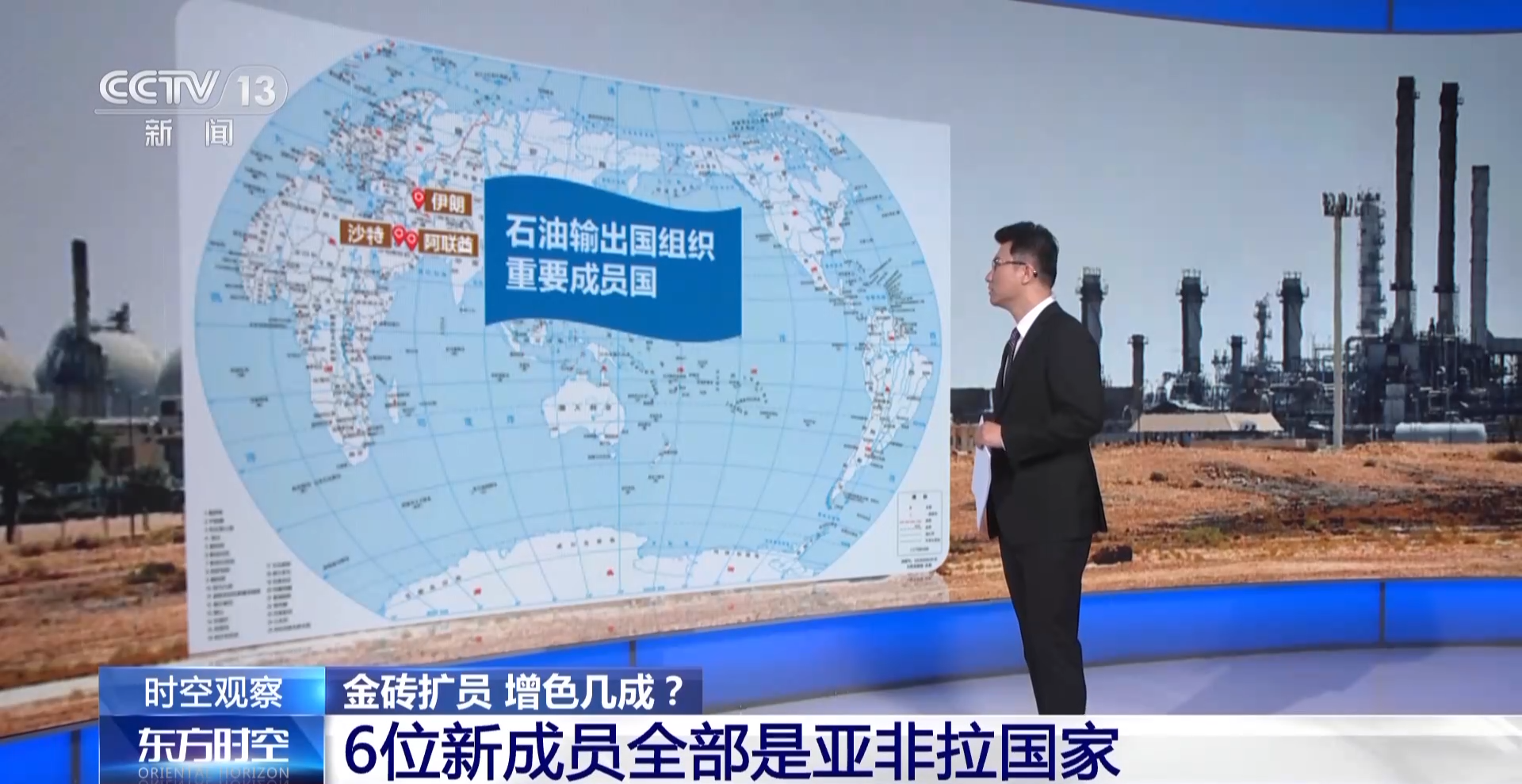中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提出“在野合作堆棧說(shuō)”,主張從理念結合堆棧開(kāi)始,到臺立法機構,再到“大選”,他還喊出“憲政”改革,要走向“雙首長(cháng)”制,最后走向臺立法機構責任制;臺灣民眾黨主席柯文哲也表示,臺灣選舉變成“民選皇帝”制,贏(yíng)者全拿,毫無(wú)制衡。朱、柯兩人說(shuō)法隔空呼應,預設了對未來(lái)政黨合作和臺立法機構體制的想象。臺灣《聯(lián)合報》今天刊文《“在野”合作堆棧,要有可操作與信任的基礎》,認為這未必做不到,但實(shí)務(wù)難度極高。
文章指出,朱柯的說(shuō)法,反映了社會(huì )對當前臺灣地區領(lǐng)導人獨大的“民主獨裁”現狀不滿(mǎn)。臺灣民眾黨沒(méi)有推上區域民代的實(shí)力,只能期待成為“三黨不過(guò)半”下的關(guān)鍵少數。尤其在“在野大聯(lián)盟”的期待下,如何發(fā)揮少數黨參政的最大利得,柯文哲因此一再提“聯(lián)合政府”。畢竟臺灣民眾黨壯大的最短路徑,就是爭取參與施政的可能。
臺灣此前從未出現過(guò)“聯(lián)合政府”。陳水扁剛上臺時(shí)任用唐飛,想創(chuàng )造“藍綠共治”空間,終因民進(jìn)黨無(wú)意與他黨分享權力,難改“朝小野大”的僵局;馬英九“執政”時(shí),因黨內紛爭,臺立法機構勢力抬頭,使馬當局施政屢受掣肘,結果以“馬王政爭”收場(chǎng);到了蔡英文,已經(jīng)完全是民進(jìn)黨一黨獨大,她把臺灣地區領(lǐng)導人的權力用盡,臺立法機構成了“橡皮圖章”。
這樣的政局不改變,臺灣“民主獨裁”的問(wèn)題不可能改變。換言之,除了“大選”,臺立法機構選舉結果也會(huì )左右未來(lái)四年的施政走向。
“在野聯(lián)盟”不僅要力阻賴(lài)清德“躺著(zhù)選”的態(tài)勢,還必須在民代選舉架構起“在野大聯(lián)盟”的臺立法機構優(yōu)勢,才能讓“在野合作”下的“大選”結果有穩定島內政局的機會(huì )。因此,“在野黨”談合作,必須先就未來(lái)行政當局的運作取得共識;若臺灣地區領(lǐng)導人不能承諾“不全拿”,“在野聯(lián)盟”就沒(méi)有合作的可能與基礎。
朱立倫拿“憲政”改革為前提,釋放出即使國民黨在選舉中勝出,也不排除在“雙首長(cháng)”制思維下,讓臺行政機構負責人成為行政最高長(cháng)官,這對臺灣民眾黨而言當然有吸引力,也是柯文哲拋出“聯(lián)合政府”說(shuō)的根本用意。
問(wèn)題是,如果雙方不能有一定默契,乃至白紙黑字的盟約,藍白合的工程難度仍然很高。
藍白合不僅是“大選”的現實(shí)需要,力阻綠營(yíng)在臺立法機構席次過(guò)半也是民代選舉的重要目標。臺灣民眾黨在區域民代提名者有限,只能寄望不分區能有斬獲;國民黨為促成合作,許多選區都預留合作空間,但多半“只做不說(shuō)”。然而兩黨合作要有可以操作與信任的基礎,才能保證在“下架民進(jìn)黨”后,能夠穩定政局推動(dòng)施政。這點(diǎn),就是柯文哲一再說(shuō)的“執行力”問(wèn)題。
文章認為,朱立倫和柯文哲的喊話(huà),都是在向對方拋善意,也預設了合作的空間。但兩黨合作,也要留有郭臺銘“共謀大計”的安排,這是朱立倫“在野大聯(lián)盟”必須克服的難關(guān)。時(shí)間緊迫,藍白兩黨除了要在政策上合作迫使民進(jìn)黨跟進(jìn)外,還要在政黨合作上有具體作為,才能翻轉政局。